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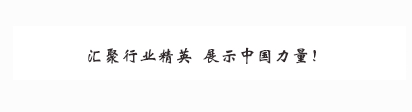 |
|
季元振 赋予建筑灵魂的工程建筑师

季元振 建筑师、工程专家、研究员、教授。 退休前曾任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执行总建筑师、副院长。 1945年出生,1961年考入清华大学建筑系。曾从事过建筑施工、建筑设计、建筑结构设计及研究、建筑教学等多领域的工作。 1987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1992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1993年获南京市“中青年拔尖人才”称号。 1993年获江苏省人民政府颁发的“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证书。 1994年调入清华大学建筑系任教。 1999年调入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从事建筑设计工作。 2010年退休,现为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顾问。
相同的史料、相反的解读 读《明清建筑二论、斗栱的起源与发展》一书有感
久闻台湾学者汉宝德先生大名,今有幸读到他的大作《明清建筑二论、斗栱的起源与发展》一书,果然名不虚传。汉先生自称是史学界的门外汉,然研究史的视野、态度和方法却俨然胜于若干史学家。汉先生的这部书分为两篇,一篇《明清建筑二论》初版于1969年,另一篇《斗拱的起源与发展》初版于1973年。去年三联书店将此两文结集在大陆出版。文章是40多年前所写,但对大陆一般人来说,仍很新。这是一本批评梁思成、林徽因先生学术观点的书。我作为梁思成先生的最后一批学生,对此当然很有兴趣。我一直在等待大陆的中国建筑史家对此书的回应,可惜久等不见。然而汉先生的“痒”病却传染给了我,不容我不写几句了。与汉先生相比,我对史学、特别是艺术史,是门外汉的门外汉,所言错误之处一定俯拾皆是,我是为了引起“争论”而写这篇短文的,因为中国建筑界的舆论总是一边倒,好没有趣味。
一、明清时期南方民间建筑的兴起
汉先生书的价值是不容置疑的,其价值就在于他对于中国皇家建筑自唐宋至明清的演变史的解读不同于梁思成、林徽因先生。汉先生正确地指出,自南宋之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至江浙一带,经济的繁荣、民间财富的积累使得民间建筑在南方迅速地得到发展。南方自古以来天高皇帝远,南方普通百姓和一般中产阶级有着不同于皇权强大统治力的北方人的观念(近百年来,凡新思想都出于南方人士,从康、梁到孙中山,笔者)。又因南方多山水,地势复杂多变,民间建筑与北方大平原的以“三合院”、“四合院”为代表的住宅,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形态。其平面布局更生活化、功能更人性化,更反映了江南文人雅士的情趣。为适应这种生活,明清时代的工匠在建筑结构、营造方法上有诸多改进,结构不再僵化,可随功能与地势而变,其取得的成就甚至超过同期的欧洲,为现代主义者、如赖特等人的大力推崇。所以汉先生不同意梁思成等《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仁们在研究皇家建筑时所得出的结论,即“中国建筑自唐宋至明清是一个盛极而衰的过程”。汉先生要为明清六百年的工匠鸣不平,还原一部真实的中国建筑史。对此我要为汉先生大唱赞歌!在研究南方建筑时,汉先生谈到了计成的《园冶》和文震亨的《长物志》,他认为计成、文震亨所代表的思想是“向已推演了上千年的宫廷与工匠传统的挑战,其历史重要性不下于西欧文艺复兴时读书人向中世纪教会御用工匠传统的挑战。这是艺术知性化的先声。”
这段话写得何其好呵!还有更妙之处,他读明清文人关于建筑的言论,不仅看见他们追求“平凡而淡雅”、“简单与实甪”、“整体环境的概念”的进步性(如汉先生所说,这种大胆丢开宫廷与伦理本位的形式主义又厌弃工匠之俗的思想是很容易自然地发展成现代功能主义思想的);还看见了中国文人的病态心理,他说:“而‘士人学而优则仕’,中国读书人永远没有与官家脱离干系,因而官家的诸制度,无不或多或少地潜存在每个读书人的心中…,因此之故,我国士人,或多或少有两面人的个性…,他们歌颂自然,与友人酬和退隐的闲情雅致,但心理上常常随时准备接受宫廷的任命。财富和名祿并不能轻易为大自然的景色所取代。”所以从当时的一些文人笔记中,可以看见他们对官式建筑的“雕梁画栋”的美赞和对官式“构造做法”的因袭。另外,我特别赞赏的是汉先生的如下观点:他说,“中国文人对建筑敏感度,直接来自文人的艺术-文学、绘画与金石。因此,文人艺术中所拥有的缺点也不折不扣地带到建筑里来。” “文人艺术的性格属于心性之陶冶,…,是在现实残酷的生活中一种求慰藉的方法,…”而“建筑作为一门艺术,需要高度的敏感。对大自然、对环境、对空间、对材料都要有适当美的斟酙。但这种敏感绝不能超出于实存的物质环境之外,亦就是说,建筑是与现实脱不开的。”汉先生在这里划清了建筑艺术与绘画艺术、文学艺术的界限,而这种两者不分的现象在当今中国建筑现状中仍屡见不鲜。
二、“梁、林”学说与“汉”学说分歧的焦点
首先必须说明的是,汉宝德先生对中国皇家建筑史的新观点,绝非因为有了新的考古发现足以推翻梁思成与林徽因先生对中国建筑演变规律的认知,而是在双方都认可的史实基础上,由于双方各自不同的学派立场而产生的学派之争;是相同的史实、不同的解读。这个争论的本身就在揭示一个真理:建筑作为时代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和技术的载体,其本身就是充满矛盾的。建筑具有二重性,它在人类的自我实现和追求技术的最大进步之间摇摆不定。所以直到今天,反映着人类对建筑理解不同而产生的不同学派之间的争论在世界范围内仍持续不断,只有这样的争论才能促进学科的发展。所以我非常高兴地看见汉先生的、不同于梁先生的对中国建筑研究的成果。它让我们有了新的视角,新的不同于梁先生的价值观。
双方的这种争论起码可以溯源到19世纪的欧洲。“梁、林”的学术背景是“结构理性主义”的现代派,而“汉”的学术背景是“后现代主义”的。在书中,汉先生说:“形式主义”产生于文艺复兴之后,而为现代建筑师所唾弃。晚今名家之主张恢复形式之精神者,以文丘里为代表。如果你明瞭了这个背景,再来看这个分歧,就会十分清楚,不再会人云亦云了。为了便于讨论,下面具体地介绍一下在中国皇家建筑艺术性上双方的分歧焦点,这个焦点产生在对“斗栱”作用的不同看法上(当然还有其它分歧,本文不做重点):
书中引用了林徽因先生的观点,汉先生认为她把中国建筑的木结构作为研究中国建筑的关键是片面的。汉先生认为从结构合理性的角度来看明清建筑,“我们必须承认,他们(指梁、林)所下的结论是正确的。明清的宫殿建筑,与唐宋建筑比较起来,在间架制度上,是日益僵化了,在木架结构上,是日渐装饰化了。如果用林徽因的话来说,‘由南宋而元而明而清八百余年间,结构上的变化,无疑均趋向退步。’”关于这种退步,在讨论“斗栱”时,书中仍然引用了林先生的原话:“插图七是辽宋元明清斗拱比较图,不必细看,即可见其(一)由大而小;(二)由简而繁;(三)由雄壮而纤小;(四)由结构的而装饰的;(五)由真结构而成假刻的部分如昂部;(六)分部由疏朗而繁密。”对这几句话,汉先生承认这是事实,但他对林先生下面一段话产生了反感,“(明清斗栱)不止全没有结构价值,本身反成了额枋上的重累,比起宋建,雄壮豪劲相差太多了。”这里林先生表达的思想是:从唐至明清,无论在结构合理性还是在艺术性方面都是全面的倒退。
对林先生的上述看法,汉先生认为不能同意。书中表明了汉先生如下的观点:
1, 他认为 :“我国建筑之斗栱系统,本身是一种装饰,是一种宫廷建筑特有的东西。它本不真正是建筑结构中有机的一部分。换言之,即使没有斗栱,我国木系统仍可存在,出檐的深度亦可存在。”也就是说,斗栱的结构性不是它的本质意义。
为了证明这个观点,他从斗栱的起源说起,他编织了一个美丽的、非常久远的神秘的故事。他说,随着汉代与西域的通商和文化交流,斗栱作为一个形象的符号传入中国,其来源可能在印度也可能在波斯,但他承认这仅是猜测没有凭据。他从一座汉墓的发掘中,发现斗栱作为一个符号可能具有一种宗教的意义,但其意义尚不清楚。总之他认为斗栱不是为了屋檐的悬挑,由工匠们特意创造出来的悬挑构件,而是具有某种象征意义的装饰,因为在他看来要实现大屋檐的悬挑,并不需要如此的繁杂、“枝丫交错”,具有装饰性的斗栱。
2, 他以现代人的眼光来分析辽、宋某些实例中的某些斗栱,发现个别部件并不是结构的需要(《中国营造学社》包括梁思成本人在调查中早已发现此现象),以此为据,他认为斗拱的装饰性作用大于其结构性作用。换言之,他企图证明清代斗栱几乎完全演变成装饰的现象的正当性。
3, 他认为:“斗栱在中国建筑史上的演变,从未达到真正‘成熟’的时期。”他认为“系统化发生在唐代,格式化发生在宋代,结构与造型同时恰到好处的时代从不曾有过。”汉先生否认“唐构”是中国皇家建筑的顶峯。
4, 那么汉先生认为中国皇家建筑的完美形式产生在什么年代呢?他认为产生于明清。他认为斗栱“饰带化”是“形式意志”的需要,他在书中将“中和殿”的立面图与“希腊宙斯神庙”的立面图相比较,他把饰带化的斗栱比着神庙檐下的饰带。这种比较说明了汉先生的审美倾向。汉先生认为这种“饰带化”倾向可能随文化交流来自西方。
从以上所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双方的争论焦点不是技术性的,而是审美的。其分歧在于:
1, 汉先生认为建筑之美主要是形式之美,形式美有“形式意志”,牺牲结构的某些合理性,对建筑艺术性来说无伤大雅。而林先生认为建筑之美必须是建立在合理的结构之上的形式之美。林先生认为在唐代我国工匠已经创造了这样的建筑型制,不仅结构合理、而且雄壮豪劲,达到了技术与艺术完美结合的理想;林先生认为从唐至清,不仅结构性在衰落而且形式愈趋纤弱和繁琐,艺术性也在不断的衰落,于是梁先生和她提出唐代是我国建筑艺术顶峯之说。
2, 汉先生认为林先生所持的《结构理性主义》的审美观是“清教徒式”的,历史上没有多少实例能做到这点,唐代没有达到这个水平。(可惜汉先生对此没有证明)
3, 汉先生与林先生的分歧实质,从艺术形式的审美情趣上来说,汉先生更喜欢装饰风格,而林先生更欣赏建筑的雄浑大气。
在我反复阅读了汉先生的文章之后,到目前为止,我仍然相信“梁、林”之说,大约我受其影响太深不能自拔。我之所以对汉先生的观点不敢苟同,有如下几点认识:
1, 汉先生的文章发表之机,正处于由美国发起的一股“后现代主义思潮”之中,汉先生的观点来源于此,他们认为坚持现代主义的理性原则的建筑师是“清教徒”。这股思潮很快被国际建筑界的许多理论家所批判,成为一个短命的流派。
2, 汉宝德先生对法国19世纪伟大的建筑理论家勒.杜克(Viollet-le-Duc)的“结构理性主义”存在着严重的偏见。他称这是“西洋人”的“大错误”。我建议大家去阅读一下肯尼思.弗兰姆普敦(Kenneth Frampton)教授的《建构文化研究》一书,看看书中对勒.杜克的评价。从书中我们可以找到“梁、林”学说的根。
3, “结构理性主义”者从来不认为结构合理会自然导向艺术美,只承认结构合理是艺术美的一个重要内容。作为结构理性主义的建构大师意大利建筑师奈尔维就曾经说过这个观点,他认为结构的合理性与艺术美之间是有差异的。所以在讨论斗栱的形式美和受力问题时,不能采取教条主义式的批评态度。汉先生在书中批判 “结构理性主义” 所谓的“错误”时,所举实例和观点:例如:“大柱应用大木材表现,小木材只能做小木柱”以及某个斗栱中的某个构件“没有结构作用”等等说法都是“庸俗的艺术唯物主义”。书中提到了某些人(如黄宝瑜的“中国建筑史”)对明清工匠用小木材拚装成大木柱做法的批评,汉先生对黄进行反击无疑是正确的。但这与“结构理性主义”无关。
4, 斗拱作为一个重要的结构构件且具有艺术美的价值,这是中国古代工匠的伟大创造。它的原型出自哪里既研究不清,也没有必要。因为从“符号”到“实体”的过程才是建筑艺术的创作过程。不可否认,大悬挑的屋檐可能还存在别的方式去完成其结构功能,但是那样的方式是否具有审美的价值就需要另行研究了,历史不能假设。例如欧洲的穹窿顶,罗马人有罗马人的做法,拜占庭人有拜占庭人的做法,哥特人有哥特人的做法。我们在研究它们的各自的建筑艺术性时,从来不会在它们之间去比较。同样我们在讨论斗栱的结构性和艺术性问题时,我们也不应该将斗栱与一个并不存在的模糊的概念去比较。这不是建筑史的方法。
5, 至于斗栱究竟是其结构性重要还是其艺术性重要,这样的命题本身就是一个圈套。这是一体的两面,既不能分离也无法分离。
6, 对于现仅存的中国唐构,无论是“奈良的唐招提寺金堂”(按梁先生的说法,在唐代仅属二流水平)还是“佛光寺大殿”(唐代的三流水平),在我看来都比清式官衙要美,也许我的审美情趣早已受到梁先生和林先生的熏陶。我以为这里的美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形式之美,一是结构之美。在“唐招提寺金堂”中,其斗拱的设计既精巧又合理,完全没有“枝丫交错”繁杂的感觉,可以说得上是上品。所以我不能同意汉先生所说:“斗栱在中国建筑史上的演变,从未达到真正‘成熟’的时期。”我也不能同意他的说法:在中国“结构与造型同时好的时代从未有过。” 我以为这个时期可能就在唐朝,可惜的是“唐构”遗存太少了,所留建筑体量都不大,真正宏大的建筑是否达到了完美,实在只能凭各人自己去想象了。所以在皇家建筑演变史上,两种学说恐将并存,成为一个谜,因为唐朝的建筑几乎不复存在。
三、关于梁先生的史学研究方法
汉宝德在书中对《中国营造学社》及梁思成先生等学人研究中国古建筑史的方法提出批评。他说:“我们应该以较具体而遗物众多的明清建筑开始,探究我国建筑在形式以外的成就,以及它怎样满足了当时社会群众的需要。从这些研究为起点,我们有希望上推至唐宋,来构建一个社会史、建筑史、考古学三方面融通的学问框架,而:汇成我国文化史研究的大业中。若不作为是想,则我国建筑史的研究,充其量只是技术史的讨论,或考古的调查,枝枝叶叶,零零星星。等而下之,研究之成果被执业建筑师所剽窃,或径用为抄袭之蓝本。”
汉先生的这一段文字暴露出了汉先生对历史研究方法的极为片面和狭隘的一面。关于历史的研究,可以有很多的视角,有各个层面、各种内容和各种方法。要想构建一个社会史、建筑史、考古学三方面融通的学问框架,它绝不是《中国营造学社》所能做到的事,更不是作为一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可能做的事。研究古代建筑史从近代建筑研究起,再开始上推至古代,这种说法毫无历史的依据。
19世纪的欧洲不少学者开始系统地研究欧洲古代建筑时,都是从考古入手的。对欧洲建筑史做出过重大贡献的,我知道的就有:卡尔.博迪舍(Karl Botticher)对古希腊建筑的研究,勒.杜克(Viollet-le-Duc)对哥特建筑的研究,奧古斯特.舒瓦齐对希腊建筑史和哥特建筑史的研究等,他们无一不从考古入手。在文艺复兴时期研究古典建筑更是考古成风。换言之,不从考古入手,古代史是无法研究的。至于在研究的初期,其成果“枝枝叶叶”、“零零星星”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事情总要一点一点地做起来,《中国营造学社》就是这样做的。他们通过田野调查发现了佛光寺、应县木塔等世人不知的唐宋遗构,并从技术上找到了斗栱演变之规律,为“断代”找到了依据,初步搭建了中国皇家建筑演变的框架,其功劳到目前为止还无人超越。对他们的研究,岂是“充其量只是技术史的讨论”可以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退一万步而言,写“技术史”又有何不可?张驭寰先生完成的《中国建筑技术史》应该是功不可没的事。至于建筑史,当然应用详细的测绘图纸表达,有执业建筑师径用抄袭,与历史研究者何干?
去年有位香港学者朱涛先生写了一本书《梁思成和他的时代》,在书中多处引用汉宝德的观点批评梁思成、林徽因先生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在社会上影响极大。朱先生认为梁先生研究中国建筑史没有一个长远的规划,与汉先生的观点如出一辙。他甚至把斗栱来源西域之说(一个猜想)也用来当作批评梁先生的武器,他认为“梁先生、林先生的中国皇家建筑自唐而宋而明而清,是一个盛极而衰的过程。”是一种主观的臆断等等。对朱先生这样的治学态度我只能一笑了之,我希望他能拿出自己研究成果才好,那怕是一点点,不要完全跟着别人说。
虽然汉宝德先生对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方法的论述有片面,但是实在有可取之处。他的要“构建一个社会史、建筑史、考古学三方面融通的学问框架,而汇成我国文化史研究的大业。”的设想确实是十分有见地的主张。汉先生敏锐地感到许多人研究古建筑不过是为了抄袭,他甚为不满,我是支持他的。
但是不知汉宝德先生是否注意到:上个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中国社会处在什么样的状态之下,1931年日本占领东三省,随时都有入关的可能。国内军阀混战,政局不稳。1937年北平就失守,随即华北失守、华东失守、华南失守、华中失守,国民政府退居陪都重庆。《中国营造学社》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完成了他们对中国最重要的古建文物的田野考察和研究工作的。战争可能使千年古建毁于一旦,梁先生他们此时此刻选择在日军到达之前完成中国北方古建筑的考察是唯一现实的研究方法。朱涛先生批评梁先生在研究中国建筑之前没有傅斯年先生在语言学研究方面的一个长远规划,真是坐而论道不知深浅了。梁先生他们调查古建是有计划的,这个调查的路线是由日军制定的,他们要与日军赛跑。
梁先生解放之后处在不断地被批判之中,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就此而停顿下来,这是时代的悲剧。近二十多年来,梁先生的学生、我的老师陈志华先生所开创的“乡土建筑调查”正是在努力完成梁先生未竟之事业,为构建“中国乡土建筑与社会学、文化学相融通的历史”做基础性的工作,可惜现在仍然是举步为艰,这样的工作哪里是坐在书斋里高谈阔论者可以理解的?
四、关于斗栱由雄壮而纤小的另类思考
我想从森林资源和人口增长的角度,来考察斗栱由雄壮而纤小这个演变的历史原因。下面我将提供一组数据,从中大家一目了然地可以看见明清工匠的无奈。这组数据是我根据樊宝敏先生的《中国历代森林资源数量的确定》一文推算而得。
自唐之后我们的森林覆盖率急骤下降,其原因是人口数量的增长,为了生计人们毁林造田,伐木造房和伐薪烧炭。再加上了战争的火攻毁林和毁房。其中建筑毁林是一大原因,尤其是皇宫的建造,唐长安大明宫麟德殿的木柱直径竟达70厘米左右,需要毁掉多少原始森林?秦汉时期我国的森林覆盖率尚在46-41%,人口仅为2000-6500万。唐朝在贞观之后人口骤增,天宝十四年达到8316万人,后因安史之乱人口骤减,后恢复至5000万人左右。唐朝当时的森林覆盖率己从唐初的37%下降至唐末的33%。经五代辽宋金夏,森林覆盖率降至27%。元末明初又进一步降至26%,明末森林覆盖率已为21%,而人口却由6500万升至15000万。清代由于康熙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人口数量激增。200年间(1644-1840),人口由8164万增至41281万,到清末人口已达43189万,森林覆盖率降至15%。
根据以上数据,我提出一个指标“人均森林覆盖率”,以唐初为1,依次推算出明清之后各时期的该数值如下:明初,0.54;明末0.189(以明朝人口最多时计);清初0.348;清后期0.062-0.0469。清代大兴土木建颐和园之时,该指标约为0.05左右。这就是说,在唐朝形成屋檐出挑深远、斗栱雄劲有力的“唐风”之际时,它的“人均森林覆盖率”是清末的20倍。清末工匠由于无大木料可用,斗栱走向纤小而装饰化是必然的客观规律。史料早已表明,到明代已出现由小木料拼成大柱的现象。明初故宫所建“奉天殿”(太和殿),雷击烧毁,复建时规模大减,木料也不能再用楠木了,这些都是资源匮乏的表现。这些现象似乎在提示人们,这个古老的体系己经衰老。“唐构”的盛极而衰的原因是多层次的,木材资源的逐年递减当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历史等待着新建筑的出现,直到西洋建筑传入中国,新的结构体系的引入才使中国人摆脱了困境。
在这个衰败的过程中,我们清楚可见的是中国工匠的聪明才智,他们既要满足皇权的穷奢极侈的需求,又要面临材料的缺乏。朝廷是腐败了,工匠们转向天高皇帝远的南方民间,在那里他们抛弃了宫廷工匠的陈规陋俗,出现一片新气象。这反过来证明了:唐至明、清,皇家建筑正在衰败之中。
专家档案:
季元振建筑师、工程专家、研究员、教授。退休前曾任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执行总建筑师、副院长。
1945年出生,1961年考入清华大学建筑系。曾从事过建筑施工、建筑设计、建筑结构设计及研究、建筑教学等多领域的工作。1987年获国家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1992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1993年获南京市“中青年拔尖人才”称号。
1993年获江苏省人民政府颁发的“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证书。 1994年调入清华大学建筑系任教。
1999年调入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从事建筑设计工作。
2010年退休,现为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顾问。
近年来,他反思中国建筑界历史及现状,比较中西方传统建筑文化,介绍现代主义,对建筑原理、建筑创作、建筑教育、建筑历史、建筑师和建筑管理等问题进行评论,写了《建筑是什么》与《再问建筑是什么》两本书。他提倡“人民的、科学的、理性主义的建筑观”,抨击当今流行于建筑界的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和标新立异的奢华之风,揭露建筑业界种种腐败的社会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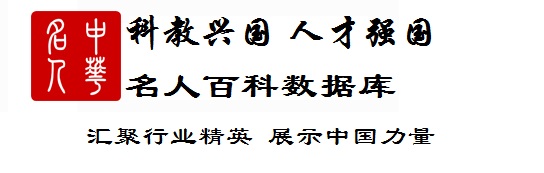
|
版权所有:重庆西促文化交流中心 渝ICP备13007947号-2 联系地址:重庆2488号信箱 联系方式:hexiexibu168@163.com |